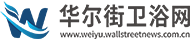2000年10月24日,美国摇滚乐队林肯公园携一张新金属乐专辑《Hybrid Theory》横空出世。2017年7月20日,主唱查斯特·贝宁顿自缢身亡,年仅41岁。2023年4月7日,乐队第2张录音室专辑《Meteora》发行20周年纪念版,收录了过去未公开的曲目。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写林肯公园的文章很难,因为他们曾经是我最重要的音乐启蒙。尽管乐队中其他成员的气质和意志共同构成了林肯公园的音效和人格,但是查斯特是难以磨灭的存在。他的歌词、他清脆的嗓音和他的音乐人格转换,都构成了林肯公园在我心中留下的烙印。借这篇文章,我想从查斯特的个人经历出发,分享他从受难者到音乐圣人的人格转换,并给出林肯公园为何感染人的解释。
查斯特于1976年3月20日出生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父母在幼年离异,因而成长在很糟的环境里,更重要的是被年长的男性侵犯,从7岁持续到13岁。性侵和家中的情形让他想要“灭了所有人,然后离开”。为了安慰自己,他画画、写诗和写歌,并他开始滥用酒精和各种违禁药品。在高中,他还被霸凌。
在经历了早期的音乐尝试后,他和林肯公园前身的Xero(由麦克·信田等人组成)走到一起。经过磨合和四处碰壁后,他们终于和华纳签约,并发行了“Hybrid Theory”(这曾是他们用过的乐队名)为专辑名的首张专辑,这张新金属风格的专辑成为21世纪销量最高的出道专辑。
新金属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的曲风,早期代表乐队包括Korn和Limp Bizkit。彼时的美国乐坛开始被Nirvana等乐队引发的grunge旋风所统治,一首《Smells Like Teen Spirits》将青少年在暴力和不安的社会现实面前的感触赤裸裸地展露出来。这种曲风往往带有颓废、边缘感和自毁式的燃烧,是痛苦和叛逆的口号,不论是唱还是听这种歌首先就是发泄,因而这种曲风的歌曲中脏话连篇。
这种曲风也对社会治安造成了威胁。Limp Bizkit的演唱会便是一个例子,各种暴力和侵犯事件层出不穷,在肮脏的地方办演唱会,听演唱会的人心脏病突发去世,这些都对普罗大众而言构成了威胁。但它也昭示着一个更为撕裂的社会现状,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层出不穷,社会失范愈演愈烈。所以,新金属和过去的摇滚乐一样,都是熔岩中迸发出的力量,充满能量,响应了一代人的精神需求和生命姿态,又极具破坏性。
主流对于这样的曲风,最初的态度非常消极,根据上述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无数音乐媒体对此表达恶评,如NME。尽管销量十分爆炸(如Limp Bizkit连着两张专辑在美国都是七八百万张的销量,还有首周破百万的纪录),但是无论是乐评还是主流奖项似乎都没法表彰这样的曲风。
正在这时,林肯公园出现了。林肯公园一个最大的卖点是“没有脏话”。尽管是颓废,但是这种颓废是从自我出发的、内向的,而非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而且从演唱到写作也相当的工整。所以,林肯公园成为那一批新金属乐队中率先拿格莱美音乐类奖项的乐队,在2002年凭借《Crawling》拿下最佳硬摇滚演奏(格莱美始终没有设置新金属这种分类奖项)。对于一种新的曲风,格莱美采取的态度通常是观望,只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出现,将对这一曲风的表彰放到某个具体的作品和人身上,所以林肯公园自然地符合这一点。
《Crawling》是《混合理论》中很重要的一首歌,也是查斯特去世前最后一次露面唱的歌。在这张专辑中,查斯特的人格表现为人在重大痛苦和创伤面前的失序和爆破。比如写性侵的《Crawling》中的“Crawling in my skin/These wounds they will not heal/Here inside my bones/Confusing what is real”,喊着痛苦无法愈合,我无法感受这个世界(因为我对世界的触碰被痛苦所包围)。还有《In the end》中“I tried so hard/And got so far/But in the end/It doesn't even matter/I had to fall/To lose it all/But in the end/It doesn't even matter”,唱着不论我怎么努力,最终仍是徒劳,过去的我像是一张巨大的网,将我捕获,无法逃脱。
伤痛久了的人,往往会带上一种思维定势,这种定势会让他走上无法信任、渴望联结、继续受伤、回到以往、加深痛苦的循环中,破坏他的心理状态、人际关系和内心的信念。而查斯特音乐人格的起点便是如此,他的绝望和挣扎和新金属的时代之声相融合。在2002年和《滚石》的一次访谈中,查斯特说自己时常会陷入到自己很可怜的自我认知里,但他觉得自己要为此承担责任。他的歌是在和自己对话,所以都是用“我”写就的,而不是“你”,因为责任方在自己,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走出来。
在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里,主人公无厘头的呢喃像是坏掉的钟表,发出离调的声响。所以他无法停止这种痛苦的表达,这是一种“失语”,尽管他没有停止表达。我想在《混合理论》中的查斯特也是这样。他的表达奠定了他痛苦而内省的精神内核。他是个善良而温暖的人,他本不是痛苦的过错方,却要背负着解决痛苦的责任,这便是世间的参差。他一直在和自己对话,只是在不断更换着角度。
到了《Meteora》,他的人格有了一定的进化。比起沉湎于痛苦的搏斗,他开始表达出想要脱离这种状态的决心。比如在《Numb》中他唱:“And I know/I may end up failing too/But I know/You were just like me/with someone disappointed in you”,就算我失败,我也不会成为像你一样的人;《Breaking this habit》中,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一个没有希望、时刻搏斗、迷茫困惑、失去意义感和表达能力的循环,他虽然不知道摆脱的办法,但他下了十足的决心;《Somewhere I Belong》中,他说除非痛苦愈合,否则无法感知一切,他要由自己完成征途(do this on my own)、展翅高飞(break away)、找到自我(find myself today)。尽管仍在痛苦,而且仍是在和自己对话,但是他在求新、求变。这是他希望感的建立。但是这种希望感,仍建立在对痛苦的深深觉察上——如果我没那么痛苦,我就不需要一遍遍说着改变的宣言。但至少,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还有这样的力量,去做这样的转变。
第3张专辑和第4张专辑上,林肯公园有了深刻的变化。彼时新金属在越战阴霾的颓废之风下达到顶峰后和post-grunge等曲风一同湮灭,新金属作为一个流派也总是十分尴尬。对于一个凭借新潮曲风成名的乐队来讲,为了巩固职业的商业和合法性基础,一个做法便是向更为成熟而老道的曲风转型。不论是市场的变化、从乐队到市场受众年龄心态的变化,抑或是查斯特本人的心态进入新阶段, 他们不仅在音乐上选择更受认可的硬摇滚,还涉及了多个人类议题。查斯特的人格,此时也从边缘的受难者变为圣人。
这点在《Iridescent》中体现的非常明显。他开始用“你”来写歌了。当你站在废墟面前,感到毫无希望,请记住一切沮丧和悲伤,就此放手。“let it go”的层层和声将“圣人”光芒降临的气息扩大,痛苦是重要的,他构成了我自己,我的一切体验,但我也要放手。正是这种要忘掉却又不想忘的矛盾和纠结,才让他需要在“圣人”的人格下以救赎者身份拯救自己。这种力量在他心中始终都有,但如果无法将两个自己切断,也许就无法走出那一步。
但问题是,他有被治愈吗?当然治愈可能难以发生,只能起起落落、细水长流,但是他在这两张专辑里的状态,是一种假强大。这种强大虽然能带来一时的力量,却也在深深地消耗自己。当能量终于撑不出了,人会迎来更深的落寞,甚至生命秩序的崩塌。
第5、6张专辑的林肯公园先后玩起电音和重回硬摇滚,体现了他们在乐坛中的尴尬局面。当潮流退潮后,依潮而起的人总要找到合适的方式存活下去,否则被淘汰。赶风潮和守旧都可能一败涂地。索性林肯公园的粉丝基数够大,能够挺住一些。
第7张专辑《One More Light》是查斯特生前的最后一张专辑。嗓子退化,已不再是那个像利刃一样的嗓音,生命更一再消磨。他说自己仍在坚持,但是生命为什么这么沉重(《Heavy》),又戴上了盔甲,漫漫长路,答案仍在前方(《Battle Symphony》)。同名曲中的他,自我价值感已然到了最低,“谁又在意万千星河中一束光的消失,或是谁的生命走到尽头”。他在众人面前演了一辈子痛苦而自强的戏目,如今他打破第四面墙,和听歌的人对话,“你们在意我吗?”于是,这个搏斗了一生的男人,最终选择了死亡。
查斯特的音乐人格之旅就此讲到这里。林肯公园的歌词不只是查斯特一人写就,还有麦克·信田,但我想查斯特的印迹是深厚的,所以我借助歌词和音乐来分析他,也是林肯公园音乐人格的变化。他从悲伤和痛苦中孕育出坚韧的力量,这种力量本身又成了某种意义的诅咒,因为和痛苦一体两面。他的内省让他始终伤害自己,又从自己身上找寻力量,下定决心,迎接挑战。他从边缘的受害者到拯救世人以拯救自我的圣人,再到力量耗尽,就算到生命终点仍坚持和生命顽强对抗,我想他不是失败者,他的精神和我们同在。